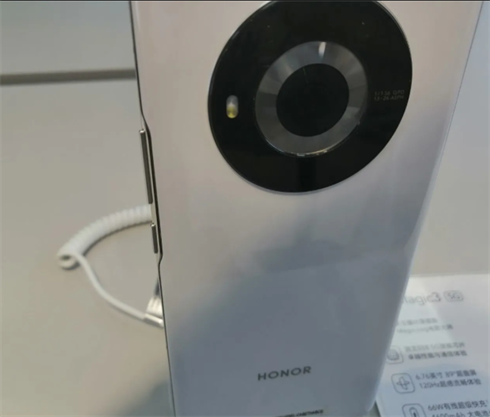这两天,中国政法大学一名法学界知名的老教授声讨另一名同样在法学界知名的年轻教授的“公开绝交信”,登上了网络热搜。
据发出“公开绝交信”的刘玫教授说,她要绝交的对象汪海燕教授,在过去的20多年间,从留校任教到编写各类教材,从各级的职称评定、博士生导师资格认定,再到副院长、院长的任职,都是经由她一手提携、力排众议才得以顺利圆满的。
但汪教授却在确定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的人选时,不懂得感恩,阳奉阴违,假传圣旨,结果是自己获选,而又把刘教授落选的责任推给研究会的领导。
教师之间的内部矛盾挂到互联网上,就成了公共事件。
评判公共事件的前提,是要有双方发言。现在只有一方发言,另一方尚未回应。
因此,要合理、客观地评判事件所涉及的两位当事人之间的是与非,还时机未到。
不过,网友的言论虽不免隔岸观火,也部分地反映出社会舆论的倾向。
让刘教授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行文态度和措辞方式,引起的不是同情而是反感。
整个舆论不是同情刘教授的遭遇,而是站在不同立场对他们俩的谴责。
极端化最容易形成舆论的漩涡,所以即便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感恩”,也会被理解成愚昧守旧;需要继承的对年长者尊重的传统,也变成了对老年人的声讨。
平心而论,媒体或网络对于大学校园里负面新闻的哗然,正说明此类事件并不算多,所以才有“新闻价值”;同时也说明,社会对于大学教育还寄托着希望,仍然把大学教师当成道德水平较高的群体看待。
因此,同居热搜榜上的郑州大学一名教师在校内核酸检测时,醉酒、插队、打人的视频中,劝架的青年志愿者才会高声提醒:“都是老师,你们就是这样给学生做表率的吗?!”
教师给学生做“表率”在过去是天经地义的,教师的社会角色就是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但是,这些年,在大学里讲“表率”已经十分罕见,所以志愿者的提醒固然掷地有声,会不会给那名违规、违法的教师内心以震慑,却很难说。
表率就是垂范、示范,属于“言传”之外的“身教”。它与传统道德自上而下的实施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当今大学教师之所以缺乏“表率”意识,当然有对于空话、套话反拨的一面,但其中的原因,却绝不止于此。
“身教”,讲的是“行”。不同于“知”,对于“行”的优劣是由他人来判断的。“行”得正,“说”才有效力,反之,屡屡“说”而不“行”,不仅没有效力,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故古人始终强调“知行合一”。
但在如今的大学里,“知”“行”分离的现象太普遍,大大影响了“表率”的提倡和开展。
而刘教授的不当之“行”,说明她实际并不真“知”。因为她的施恩均表现在替人谋名、争权之上,而她所要求的“知恩图报”,也是在为自己争名夺利。
从理论上说,要做“表率”,眼光就须朝下,注意接受表率者的反应是关键。
就好比教师讲课,只管自己讲,完全不顾学生的反应,只能说是自我感觉良好,绝不能算是教学好。
可是,由行政主导的教学管理,正在让“教学好”的教师角色变得泛化。
讲不好课的人,可以通过申请或参与教学改革项目而成为“优秀教学奖”获得者,没有承担或极少承担教学任务者,也可以得到“优秀教师”的称号。
这等于是鼓励教师眼光朝上,奔着荣誉和利益去“要”。而一旦眼光朝上,教师也就由原来的“授”转变成现在的“受”。
“受”之人,是居下者;而居下者因为没有“表率”的义务,自然不会有“表率”的预期和自律。
大学的培训化倾向则进一步让教师的角色发生转变。因以技术、技能、职业培训为主,教师与学生之间逐渐成了知识有偿服务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中,教师只是一个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服务员,按需授课,按劳取酬。
彼此地位平等,也没有“表率”的必要。
从志愿者的提醒也可以看出一种期待上的错位。在一般人或学生的眼里,教师应该是给学生做表率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学的氛围和机制正在让教师失去原有的角色认同。
因为在大学里,教师不再是“主人翁”,只不过是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教书职业,固然不比他人卑贱,但也不比他人高尚,因而是否具备“表率”的资格也成了一个问题。
至少在自我意识中,那个做“表率”的角色似乎是在渐行渐远的。
没有“表率”意识,就不会对自身有所要求,对自身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也难以作出清晰的预判,即便像刘玫教授这样行内知名的老教授也不能幸免。
因此,面对“公开绝交信”,人们同样有理由发出“都是老师,你们就是这样给学生做表率的吗”式的质疑。
由于过分“行政化”带来的等级制和极端“公司化”带来的经济差距,让大学不再是理想主义者诗意的栖息之地。
而只有现实主义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博弈的场所,是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斯文”的。
因此,对大学过于理想化的期待只能让“知”“行”分离或无“知”无“行”变得越来越明显。
刘玫教授从教40余年,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二级教授,还要为一个二级学会的副会长而公开绝交。
抛开名利不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哪怕是校内仅次于资深教授的文科二级教授,仿佛也感觉不到应有的尊重。
因此,现实地看,既然表率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自上而下的,那么提高每位教师的实际地位,让教师成为学校的真正主人(而不是为生存需要的打工者),就是当务之急。
只有令人尊重,才能产生榜样意识,也才会愿意为做表率而超越自我。
当然,“教师”对较高道德水平的追求,不仅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期许,也应该是一个自我要求,行内知名的教授更应如此。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