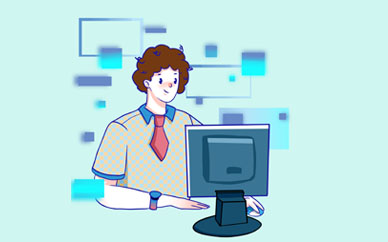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倪思洁
李献华的名字一次次走进公众视线,与月壤研究有关。
2021年,他带领团队,用0.15克月壤,7天完成分析,16天论文完稿,100天在Nature上同时发表3篇文章,将科学界认知的月球岩浆活动结束时间推迟了8亿至9亿年。
这堪称月壤研究的“中国速度”。
日前,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科协等部门组织开展的2022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献华名列其中。
近日,《中国科学报》对话李献华,他聊起了与月壤的“亲密接触”,讲述了月壤研究“中国速度”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也为年轻人如何应对“内卷”焦虑,如何做出高水平论文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月壤太细了” “我们在和历史赛跑”
《中国科学报》:您拿到月壤样品时是什么感觉?
李献华:第一次看到月壤的那一刻,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月壤太细了!
这些样品有多细呢?我们平时能买到的最细的精面粉,是100到120微米,月壤的平均粒度比精面粉还细,只有50微米。
我们做地球样品研究的时候,会采集很大的岩石样品做各种分析,这次拿到的月壤装在小瓶子里,我们申请的三克月壤来自两个编号的样品,装在两个小瓶子里,一瓶装了一克,另外一瓶装了两克。
所以我们就拿着样品不敢轻易打开瓶盖,因为很多很细的颗粒不只是会粘在玻璃壁上,也有可能会“飘出”瓶外。
《中国科学报》:一般认为,科学研究拼速度是为了获得发现的优先权,当时您和您的团队拿到了月壤,已经占据了样品优势,为什么还会那么着急地去做分析、发文章?
李献华:我们在和历史赛跑。
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任务首次取回月球样品,9月美国宇航局把样品分发给了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科学家。
我的博士生合作导师Tatsmoto教授负责了阿波罗11号月岩样品的U-Pb同位素定年研究。
1970年1月在《科学》杂志上出版了一个专辑系统报道了阿波罗11号的研究成果。所以,他们9月份拿到样品,1月份发表文章,差不多只用了4个月时间。
拿到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回到研究所之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启动会,所长吴福元院士要求我们“目标明确、方案周密、紧张有序、协同奋战”,一个星期内完成定年、岩石地球化学、水含量和锶、钕、氢同位素分析,然后再用一个星期时间写成文章投稿。
当时,全世界都在等着我们嫦娥五号样品的研究结果,希望能知道嫦娥五号月壤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月球新故事”。
中国科学家能在拿到样品之后很快、很好地得出研究结果,这本身也展示了我国月球样品研究的学术实力。
用0.1669克阿波罗月尘做过演练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吴院士给出的要求是“一个星期”,而不是更短或更长呢?
李献华:这个要求是有道理的,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故事。
我们所的标本博物馆里,有一个“阿波罗月尘”样品,这个样品身世不明。大家只知道是1971年保存在所里的,放了50年。
在拿到嫦娥五号月壤样品之前,也就是2021年的春节前,吴福元所长把阿波罗月尘样品交给我,要我们通过分析研究回答几个问题:这个样品到底是不是月壤样品,是不是阿波罗任务采样回来的,如果是阿波罗任务采样回来的样品,那么它是阿波罗哪次任务采样回来的。
对这个样品的分析相当于一次演练。样品很少,只有166.9毫克,我们的研究团队,就围着这166.9毫克样品开始工作了。
当时没有做月壤分析的经验,用了两个星期把结果做出来了,证明这个月尘样品是阿波罗11号任务采集的样品。
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技术上早有储备,心里也是有底的,知道技术流程的过程和可行性,也知道我们大概能做得多快多好。
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结果、发表文章,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团队精神和建制化的工作模式。
在拿到月壤样品之前,我们已提前把相关的仪器设备调试到了最佳状态,在月壤样品研究过程中,所里其他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用这些仪器设备,为月壤样品研究开了绿灯。
我们能这么快做出结果,要特别感谢那些当时为月壤研究“让路”的同事们。
“靠牺牲健康来做科研是不应该被提倡的”
《中国科学报》:您曾为了不耽误月壤研究进度,推迟了白内障手术时间,为什么会这样?
李献华:当时实在是很不凑巧。1992年我的右眼视网膜脱落,1993年初做的手术,之后右眼视力一直不太好,所以我是靠左眼来工作的,左眼用了几十年,退化了。
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工作累了,到2020年10月份体检时才发现是白内障,那时候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快下来了,如果做白内障手术的话,要休息,还要恢复一段时间,所以我就拖了拖,结果拖了差不多快一年。
我记得去年10月19日开新闻发布会之前,我和几个团队骨干准备新闻发布会的PPT,他们都是年轻人,把PPT做得好漂亮,可是字太小了,我看不清楚。我就拜托他们把字调得再大一点,可是字太大了PPT就会不好看,开新闻发布会时大多数字我看不太清楚,只能尽量把它们记在脑子里。
《中国科学报》:前段时间,有华人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文说,后悔为科研牺牲健康。您认为,做好科研和保持健康之间是否有矛盾?
李献华:科研和健康本身并不矛盾,但在某些时候、某个特殊的条件下,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不过,我们都是平常的人,应该过平常人的生活,靠牺牲健康来做科研是不应该被提倡的。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成天熬夜,身体很重要。我现在有点羡慕年轻人,他们的精力真的很充沛。
如何延长我们工作影响的“半衰期”?
《中国科学报》:您连续多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ESI 全球地学高被引学者和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对于年轻人提高研究成果影响力,您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
李献华:能不能获得高的引用率,跟学科有关,跟工作内容也有关。
我翻看了我自己的高被引文章,第一类是新方法、新技术方面的,做科研的人都要用到相应的技术方法,如果这个技术方法是你研发的,别人用的时候当然会引用。
第二类是学科基础性的工作成果,我是做地质年代学研究的,年龄是最基础的工作,做任何一件事情,人们会首先关注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能被高被引还有一个原因,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正好是大陆动力学学科快速发展的时候,我赶上“热潮”了。
高引用是工作扎实与否的客观反映。你的工作做得扎实,自然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所以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要研究专业领域里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工作要做得扎实。只有扎实的工作,才能延长我们科研成果影响力的“半衰期”。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自己“正好赶上了学科发展的热潮”,您是怎么进入这个学科的?
李献华:我1979年高中毕业,高考分数不错,中国科技大学的招生老师就到我们中学来,说“你的考分可以上科大,你的各科成绩我看了,可以选择地球和空间科学系、生物系和近代力学系”,当时班主任老师说“当然选地球和空间科学系好!将来可以到太空、到月球上去”,我就“稀里糊涂”地选了这个专业。
后来,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看了一本叫《月质学研究进展》的书,讲月球的,很有趣。
1983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我就去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欧阳自远老师的天体化学专业,没想到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所里报到的时候,所里说报欧阳老师的学生太多了,把我调剂到了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
前不久,我跟欧阳老师还聊起了这件事,我跟他说“欧阳老师,当年我考你研究生的时候你没收我,现在我要做月壤研究了,你可得重新教我了”,欧阳老师也笑了。绕了40年,我还是绕回了月球研究。
“视野开阔了,就不会那么焦虑”
《中国科学报》:每个年代的人都有每个年代人的难处,现在年轻科学家面临的难处可能就是“内卷”带来的焦虑。您遇到过类似的焦虑问题吗?
李献华:“内卷”是科研生态的问题。现在年轻人似乎有很多焦虑,为什么?我觉得焦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挑战太多。有时候你越着急,就会越欲速不达,稍微看淡一点,水到渠成会更好一点。
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的挑战。我认为“挑战”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我们常常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生活和工作一点挑战都没有,好像也没啥劲,因为也没有机遇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挑战过于严厉了,你放弃一下也没关系,但如果一遇到挑战就放弃,那就是“躺平”了,放弃挑战,也就放弃了可能获得的机遇。另外,我们期待的东西要跟自己的付出相匹配。
《中国科学报》:如今您和您的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地球样品和月壤的研究,未来,您最想拿到的样品是什么?
李献华: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主要在国内做野外考察,差不多有两年多没有到国外出野外了。
疫情前的最后一次考察是在2019年9月,我去了加拿大阿卡斯达(Acasta)地区,是无人区,非常靠近北极圈。
Acasta是地球上目前已知的、唯一的有40亿年的岩石出露的地方,在那里我也见到了绚烂的极光,是很难忘的经历。
当时我还规划着要去格陵兰,那里出露了38亿年的古老岩石,但是这个行程因为疫情搁置下来了。所以,如果要问我下一次我想去哪的话,我想去那儿。
对于更远的未来就希望能够为地球科学发展做出中国地质学家应有的贡献,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想研究月球背面的样品、火星的样品,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的。
《中国科学报》:对获得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您有什么感想?
李献华:挺荣幸的,但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幸。能当选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我觉得让我能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地质学家在做什么,这是我的荣幸之所在。
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旅游,想看看这个世界,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应该来学地质,我们可以带你看全世界的山山水水、探索其中的奥秘。
做地质的人思想会很开阔,因为去的地方多了,见得也就多了,也就会“见怪不怪”,刚才你提到“焦虑”的问题,很多事情视野开阔了,心胸开阔了,就不会那么焦虑了。